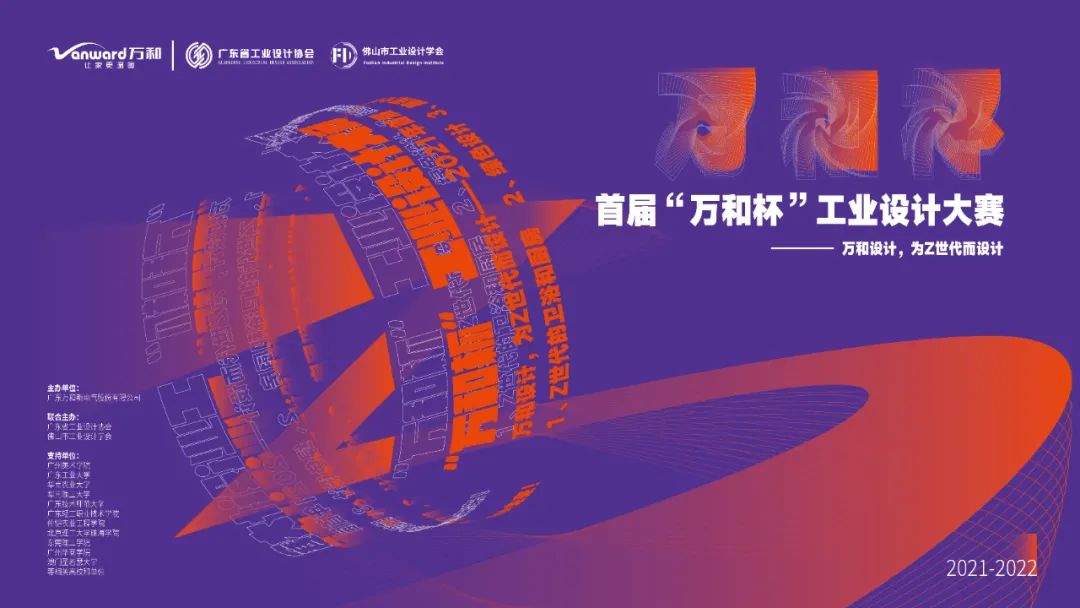柯律格访谈:我的中国艺术史思考方法与生成
9月1日和2日连续见到柯律格,第一次是在采访时,第二次是在讲座现场。这位高挑的苏格兰人穿着纯色衬衣、九分裤、深红色袜子,带着一点京腔的普通话源自上世纪70年代在北京的进修经历。时隔40年,依然“乡音”不改。

《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状况》不仅在美术史界,在文化界、历史界都有巨大影响;《中国艺术》已经成为国外很多学校的中国美术史教科书。他的著作一一被翻译成中文,其研究主要围绕着明代中国,同时也涵盖20世纪及当代艺术。他将中国艺术放在世界美术史的语境中进行研究,将美术史与中外历史发生关系,这从此次在北京的讲座题目中便可见一斑。
9月2日至4日,应OCAT研究中心的邀请,柯律格在北京为期三天的讲座以“中国艺术史上的三个跨国瞬间”为线索,集中关注20世纪的前30年,那时现代/传统、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首度被运用到中国艺术中。“1902-1903年:谢赫在加尔各答,中村不折在巴黎”“1922-1923年:董其昌在伦敦,杜里舒在北京”“1927-1928年:潘玉良在罗马,保罗·塞尚在上海”,在同一时空中,艺术家们因为地域而产生的交际,以及因此而发生的中国艺术的传播,显得格外生动而有趣。

每隔两三年他便会到中国讲学,这也让柯律格更加熟悉中国听众的“口味”。此次讲座便是为中国听众量身打造的。柯律格自己也说,虽然他的书很多被翻译成中文,但其写作的目标读者是西方人,书自然是以西方读者的阅读口味去构思的;此次的中国讲座虽然同样是用英文,但是对象是中国人,对于谢赫、董其昌、潘玉良这些名字显然比西方人要熟悉得多,而这个讲座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可以直接切入主题,而非概览似的介绍人物生平。
自2015年起,OCAT研究中心的年度讲座每年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来北京演讲,正如现任执行馆长巫鸿先生所言,这些学者可以把北京想象成生产知识的基地,针对中国的读者群,把中国做成知识生产的“原生地”。自此,这里可以成为学者们知识生产的场所,而非知识的“转译站”。
虽然柯律格因为研究中国艺术史盛名在外,但中国国内对其的采访却有限。《Scope 艺术客》杂志在讲座开始前对柯律格的采访将以自述的形式呈现,让文字成为知识最真实的“原生地”。
20世纪中国艺术对于我来说可能是一种新的尝试,但绝对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尽管我大部分的发表和著作都是关于明代艺术,但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不管是在这个苏赛克斯大学还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以及最后在牛津大学都是在教授这些课程。

西方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中一直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太多的界限了。比如有专门研究清朝中国艺术的,有专门研究民国时期中国艺术的。研究清朝的可能只看1911年以前的,对1910年之后的不感兴趣,研究民国的对1911年之前的中国艺术也是不去染指的。我想要强调的是像我们所感兴趣的、关注的那些艺术家,他们一生的经历是不能用这样的一个界限来划分的。比如金城、陈师曾等,不能说他们是清朝的,也不能说他们是民国的,他们的一生是跨越这两个历史时期的。
还有一些人是不局限于一个地点的,比如有国外经历的,他们去过欧洲或者日本。这正是我的兴趣点,我想去看一下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的一些发生,这里面就包含了很多“意外。
讲座的题目也传达了这样的理念,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这种发生都是一种意外,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穿插着发生的。我很想去探讨一下不同时间和地点之间的融汇和沟通,以及互相影响。当然这不一定完全都是在意外之外,有些可能也是在意外之内。
此次的三场讲座中的提到了非常多的、具体的人名,我提这些人名其实是作为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把我们引入到一个更大的讨论和视角。这次的讲座有点传记的性质,你会发现很多是关于谁,谁去哪了?什么时候去了?和谁说了什么?
在我职业生涯的诸多著作中,我一直在写不同的艺术史,而不是一直在写同样的一种思维的一种艺术。艺术史这个科目实在是太丰富了,绝对是有多种研究方法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有兴趣的研究和探讨的。
我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写于20年前,那本书里面就没有提到太多的名字。因为20年前的伦敦,艺术史研究不会关注个人角色,以及不同的名字,当时更为关注用不同的方法去探讨艺术史。我非常开心我们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不同的视角来审视艺术史。
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期间,不管是中方还是西方,对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发展是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的。
1970年代末,我刚到维多利亚和艾伯特博物馆(V&A)工作的时候,西方对中国20世纪艺术史的学术兴趣是非常低的。据我了解,当时的中国对这个时期的学术兴趣也是非常低的。但是这之后就有一个爆发式的发展,现在有非常多的人在研究20世纪中国艺术,而且有很多学术研究出来。
我一直在努力跟进这些研究,我会去读他们的发表或去看一些展览,想要跟进他们这方面的进展。这对我来说一直是我的一个兴趣点。
如果我们现在要去审视中国艺术史的话,很重要的途径是,我们要看一下20世纪早期,即民国早期那一代学者和知识分子给我们做出哪些贡献。
我们今天在审视中国艺术史的时候,比如说看20世纪以前中国艺术史时我们所使用的思考框架和方法,都成型于民国时期。20世纪早期有非常多的研究机构以及文人志士,他们帮助我们形成了一种审视和思考中国艺术的方式和方法,或者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
我们要了解明代的话,我们肯定要使用一些工具,不同朝代使用的工具是不一样的。我们审视和研究明代艺术的工具可以溯源到民国时期,为什么呢?民国时期的知识界对明代的艺术是非常感兴趣的,1910年代以及1920年代有非常多的人研究明代的艺术。
当我们在审视明代艺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通过成型于民国早期的一种思考框架来审视明代艺术。这对于我来说,这种联系就显得至关重要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可以构成一个非常好的研究想法和方向。
当然,这绝对不是我首次提出的想法。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研究明清的学者都有提到这样的联系,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更多地去思考文化非常繁荣的早期民国到底是如何形成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框架,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
20世纪早期有一个全球性的现象,比如说在20世纪之前没有人会去问到底是什么构成一个所谓的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到了20世纪早期,一个独有的特点是全球各地都开始追问这个问题,包括很多艺术家也在自问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艺术家有了自我的认识和自我的审视。
这种自我认识和自我审视的心情是非常有能量的。在某些地区,这个问题可能就成了艺术家意味着什么?但是这在有些地区可能就需要一个限定,在某些地方成为艺术家意味着什么?比如说在巴黎,大家的问题是成为一个艺术家意味着什么,但是在上海、北京、墨西哥城,这个问题就是在这儿成为艺术家意味着什么?从全球范围来看,关于艺术家自我审视有种分配不均、分布不均、程度不均,有些地方更关注地域性,各地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所掌握的知识或者信息,其实永远是不足够的,是不充分的。比如说西方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还不会走,就急着跑。
西方对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个非常大的框架,告诉所有人这就是中国艺术,但他们当时对中国艺术知之甚少。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面临这样的困境。我的想法是大家不要总是试图从一开始就想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整体的、纲要性的叙述,什么都想要覆盖到。
中国艺术是非常大的话题和研究领域,是分为不同阶段的,我感觉更好的状态是大家不要总是去定义一些东西,减少些定义,更多地去了解一下你在讨论的东西。
最近,我跟很多西方的中国艺术策展人集会,我们都非常有共鸣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你想要说服一个非常大的西方艺术机构来做一个关于中国艺术的展览,最终只做成概览似的展览。举个例子,你跟一位馆长说想做八大山人的展览,但是馆长不知道谁是八大山人,这基本上就做不成。这不能说是馆长的错,在欧洲这的确是一个相对普遍的现实。
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悲观的,因为西方主要艺术机构办展的思维还停留在可以办中国绘画的名作展,可以再展一次兵马俑,但是没有办法去展林风眠或者徐悲鸿。是不是能够让我们就关注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并展他的作品,来探讨他的艺术?

更多关于的新闻
- “智”造美好人生 专访欧琳集团...2010-04-12
- 李德志:项目带动是粤港合作最好...2011-03-14
- 乔纳森.伊维:苹果的竞争对手选...2012-03-13
- 尹定邦专访:关于信息时代设计的...2019-07-22
- 专访广汽研究院:世界车,中国创!2011-06-29
最新文章
- 专访|专家评审团谈“好设计”2022-09-29
- 专访|周红石:绿色意识体现在产...2022-09-29
- 嘉应学院校长杨洲教授接受梅州...2021-06-10
- 何文太丨中国设计新青年参赛作品...2021-01-12
- ICS国际色彩设计空间奖项|设计师...2021-01-12